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9.02.22 09:30~11:30
引言人:尤伯祥律師、林俊宏律師、陳奕廷律師、李佳玟教授
與會者:尤伯祥律師、黃柏彰律師、李玟旬律師、羅健瑋律師、劉耀文律師、王羽丞律師、唐德華律師、施立元律師、邱禹茵律師、林玥彣律師、史崇瑜律師、夏懷安律師、莊巧玲律師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
尤伯祥律師:這個題目最近憲法法庭剛開完公開說明會。據我觀察,憲法法庭的公開說明會很像準備程序,接近下級法院的準備程序,這個案子會不會再進行言詞辯論我不曉得,但是那一場公開說明會還蠻精彩的,我相信你們在大法官網站上面大概都有看到每一個被諮詢的團體提出的書面意見,刑辯協會提出了兩份意見,一個意見書一個補充意見書,李佳玟老師的意見書也有在上面,歡迎大家去上網下載。刑辯協會的意見執筆人是小弟在下我,稱不上學者嚴謹之作,但是一定程度上是說出了律師界的心聲,所以各位在場的道長將來如果在實務上面工作的時候,需要用到跟檢方或是跟法院對抗的理論上武器的話,歡迎參考一下我們的東西。
我們待會進行的過程會很輕鬆,我們證據法沙龍一向就是以輕鬆為主,所以這個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所以不要太嚴格看待我們待會提出來的Power…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9.02.11 19:00~21:00
引言人:Thomas Wang(王緯華顧問)
與會者:尤伯祥律師、陳明律師、左湘敏律師、李奇律師、莊巧玲律師、何承翰律師、林明勳律師、吳立瑋律師、陳昱廷律師、黃子涵律師、吳鏡瑜律師、黃柏彰律師、蔣昕佑律師、張晁綱律師、溫嘉玲律師、邱文智律師尤伯祥律師:
今天晚上這場刑辯沙龍的主題我們請Thomas來講美國的律師的事實調查的工作。Thomas自動把題目範圍擴張到證據開示,我想這是一體兩面的,你講證據調查不可能不去講證據開示,所以我想Thomas把它擴張是對的。
為什麼會安排這一場沙龍?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證據開示對我們來講是陌生的,另外一方面來講,特別是在民國91年引進了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後,對台灣的律師來說,總覺得我國跟美國的律師就證據調查的部分而言,根本不能相比。美國律師好像神通廣大、什麼事情都查得出來,但我們好像很弱。我們常常在講我國律師沒有調查權,所以我們做不到像美國律師那樣子,但後來我去查了一些相關的文獻,卻找不到什麼特別明文美國律師調查權的規定,所以我就非常好奇這個調查權到底是事實上的概念還是規範上的概念。今天剛好邀請到Thomas,他以前是美國加州的公設辯護人,所以Thomas來跟我們分享聖地牙哥那邊的律師是怎麼樣進行事實調查的,我想相當程度上可以為我們釋疑跟解惑,所以今天晚上這一場刑辯沙龍我想對大家來講一定幫助非常大,特別是對我個人一定幫助很大,之後要跟官方在講相關事情的時候比較容易講得清楚,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就很高興得邀請到Thomas來幫我們做這一場沙龍引言,接下來歡迎Thomas。Thomas…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10.4.8 19:00~21:00
引言人:王緯華顧問(Th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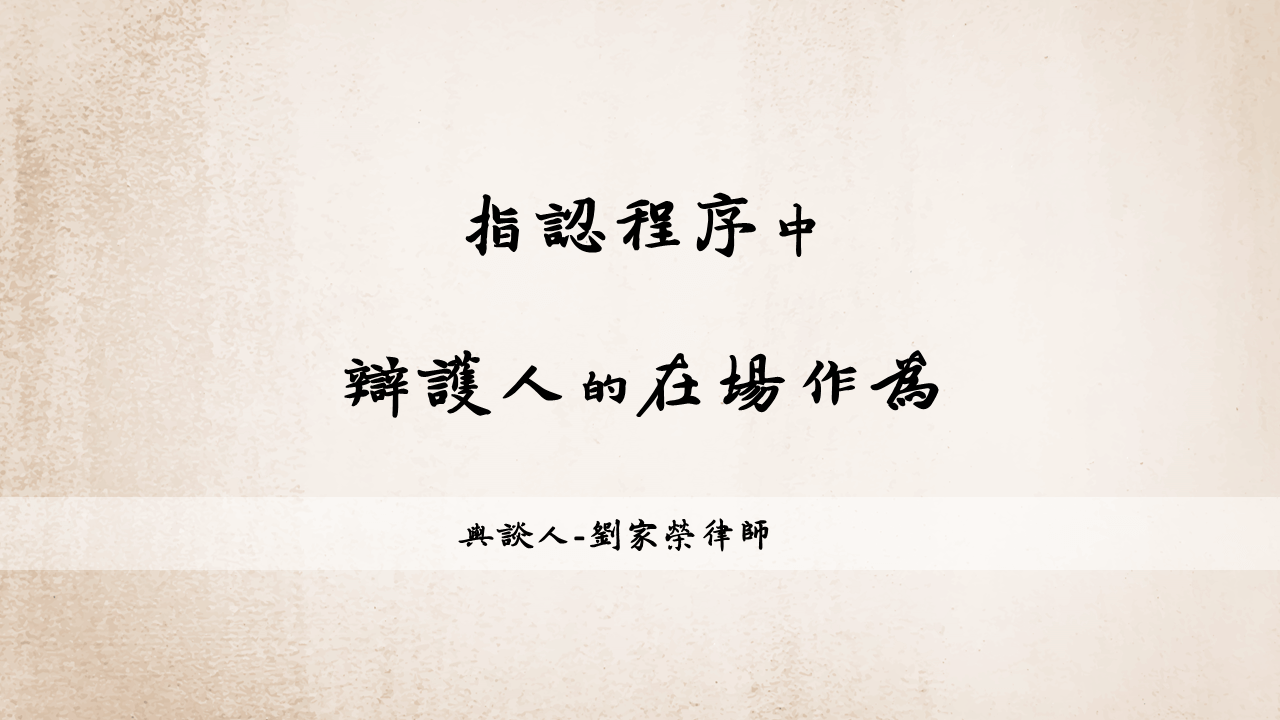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8.12.19 19:00~21:00
引言人:劉家榮律師
與會者:劉家榮律師、尤伯祥律師、陳明律師、莊巧玲律師、鄭凱鴻律師
《指認程序辯護策略與困境》
劉家榮律師:
今天是針對指認的部份跟大家討論,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大概民國95年一個很誇張的指認情形之案例,大家看一下這是我們目前的指認。(播放影片)等一下即將進入指認的情形,這是當年的很少的真人列隊指認。大家不難看到有一個只有他有手銬、穿囚服人,其他的人還可以互相對談。他們現在換人,換排然後移動。要做第二次指認增加正確性的時候,指認人本身那樣從頭到尾都站在那個地方看你挪到另一個位子,如此慢慢移過去他們換了一個牌子這樣就叫做指認實在是相當可笑。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被害人,當年的被害人有兩組,剛剛是一個女大學生,這個是一個國中生整個換位的過程完全都看到了。
所以就這個過程大家不難看得出來這個根本不是在做刑事案件的指認跟偵辦,這個在演戲,但是法官接受了這樣的演戲然後也接受這樣子具有證據能力的情況。在這個地方給大家看一下被指認人的長相、外觀跟其他人的長相、外觀是不是有顯著地不同。就光長相的部份,膚色、高度、高矮、胖瘦有沒有禿頭這都是非常誇張的,另外穿著已經很離譜了啦,只有被告身穿囚服。連這個編號2號的人還可以去罵1號說「就是你,你不要來這一套」,那這個指認人就在外面從頭到尾她沒有變過用手比1這個數字。這就是當年的指認,比照片指認還要不如的真人指認,他們要重複做第二次的指認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移動,然後指認人從頭到尾都在外面看,這樣指認有意義嗎?這個真的是在演戲不是在指認。時間的關係我們先看到這邊就好喔。我們的指認種類目前來講大概就這兩種,「真人列隊指認」以及指認「嫌疑犯紀錄表」…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8.12.14 09:30~11:30
引言人:陳奕廷律師…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8.12.14 09:30~11:30
引言人:陳奕廷律師…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8.10.19 09:30~11:30
引言人:沈元楷律師、陳明律師
與會者:陳明律師、尤伯祥律師、陳冠維律師、李奇律師、林煜騰律師、黃柏彰律師、黃上上律師、陳宥竹律師、梁巧玲律師、梁丹妮律師、江沁澤律師、史崇瑜律師、游子毅律師、湯詠煊律師、嚴心吟律師、周弘洛律師、鍾依庭律師、蕭洛森律師、陳志寧律師、江鎬佑律師、陳奕廷律師
主題二:性侵害案件証據法則的特殊性
陳明律師:
感謝大家在這麼珍貴的周末能夠撥冗來聆聽。首先讓大家看一下這一個統計表,這是從2005到2006年性侵害事件的通報案件數,這是通報而已,可以看到說約從2008年之後每年都不會少於1萬件,要個別說明是其實犯罪的黑數,也就實際上有發生但沒有通報的我認為有一定是倍數以上,從律師的角度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的案源。接著是性侵案件的定罪率,這個是法務部所做的統計數字,我是有一點點懷疑說一般案件定罪率有這麼高嗎?就是介於95到96之間,有那麼高嗎?沒關係我們就主要在這個對比,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個年度,性侵案件的定罪率都比一般案件來得低,所以性侵案件一定有一個他的特殊性,為什麼比一般案件來得低?我們來看下一張,我認為一個原因是隱匿性,因為絕大部分的性侵案件,如果是被害人是成年人他一定是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不會有在場的目擊證人,如果被害人是幼童、兒童或者是他的精神有、有障礙的話那更不用講,所以它具備有隱匿性。那第二個就是隱私性,因為這種案件涉及到私人的sexual…

僅限會員訪問
日期:108.10.19 09:30~11:30
引言人:沈元楷律師、陳明律師
與會者:陳明律師、尤伯祥律師、陳冠維律師、李奇律師、林煜騰律師、黃柏彰律師、黃上上律師、陳宥竹律師、梁巧玲律師、梁丹妮律師、江沁澤律師、史崇瑜律師、游子毅律師、湯詠煊律師、嚴心吟律師、周弘洛律師、鍾依庭律師、蕭洛森律師、陳志寧律師、江鎬佑律師、陳奕廷律師
主題一:境外證人供述之證據能力研析
沈元楷律師: 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境外證言的證據能力的問題。最近的刑事犯罪有跨境化的現象,像是掏空或跨境炒作,或熟能詳的跨境電信詐欺,再到運毒等等。 我本身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是因為我們事務所有承辦了一個案子,那個案子很巧有一個關鍵證人在美國,本來是要去做訊問,要用視訊的方式去做交互詰問,但是因為美國那邊因為有一些證據法上面的問題,美國的檢察官原本是同意的,但在過程當中知道我國證據法方面的規定跟美國有一些不一樣,經過一些爭吵最後就沒有問到,於是我就對這個問題產生了好奇。
以兩個實際案例作為一個引子。第一個是一個日本的案子,大概的事實是駕駛某甲駕著國籍的漁船去報關出海,在某海域裏面取得毒品之後,往日本海域的方向運輸,後來被日本海上自衛隊(等同我們的海巡署)查獲,那時候是由日本的人員去問,那這樣子的一個證言的證據能力是有爭議性的問題。
.
第二個是爭議更大的案件,所謂的杜氏兄弟案(杜清水、杜明郎、杜明雄),杜氏兄弟就是杜明朗跟杜明雄,那他們被控於90年7月15日在中國買了水果刀等作案工具,他們原本在大陸有一點窮途潦倒,後來有好心的台商侯國利以及葉明義收留他們讓他們在工廠裏工作,他們被控說在中國佛山先去買了水果刀然後到五金的化工廠裏面先去殺死保全員兩人,再裏面去殺害那個葉明義、侯國利還有中國女子熊玉嬋,搶得人民幣247萬餘後搭機返台,這個是他的這個一個主要的案件事實。 爭議是在於台南地院的一審其實是判無罪,主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相關的證據都在大陸那邊,台灣是沒有證據的,一審因為這樣的理由判無罪。台南高分院的二審逆轉而且判死刑,為什麼呢?二審主要採信了中國公安的蒐證,案發當地的一個計程車司機叫做付光選,付光選證明杜氏兄弟去買西瓜刀這一個事實,從此之後更一審到更六審的都維持同一見解,杜氏兄弟之前也被執行,但是因為這個案子牽涉到很多大陸這邊的證據,因此有很多人認為說這其實是一個冤案,因為你不太瞭解付光選的證據。 這個兩個案件共同凸顯出來的事情就是說:在國外或境外的證據依照當地的證據法則所做成的筆錄,究竟其證據能力是如何?杜氏兄弟案他當然是採取了中國公安的筆錄;日本的這個運毒案,有些見解是認為說這個是沒有證據能力的,,有些見解認為說這個部份其實是有證據能力的。107年第1次刑事庭決議的一個案例事實,最終其實認為說是有證據能力的,那這部份究竟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這樣子。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境外的證言、他的指證的一個方式,那可能的取證方式分為好幾種。第一種,可能在證據能力上沒有那麼大的爭議,在境內這邊直接以遠距離視訊的方式去做詢問,比如說我們如果承辦一些案件,不管是在就是偵查中或在審理當中也都有這種遠距同步視訊,那像我的話在偵查中有同步去訊問過在韓國的一個證人,這個部份算是比較直接,因為你要確保我們這邊取證的習慣或是在機關裏面進行,然後能夠確保整個過程對答還可以。那我剛剛所提到那一個案件,那是通貨案件,我原本也是打算用這樣的方式去詢問,但是可能因為兩邊就沒有喬攏,所以到最後就沒有這樣子去做; 另外一種取證方式就是偵查人員在境外直接詢問證人,他不是透過電子的方式,是偵查人員直接在境外詢問,那偵查人員在境外詢問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請求方的一個偵查人員就是直接在境外訊問證人,就依我國的例子來講...共犯,可能涉案情節非常重大,所以他不願意回台灣,就像很多經濟犯罪的當事人一樣,他擔心回國來之後就出不了,所以他採取什麼樣的變動方法呢?他在香港的機場的過境室裏面,我們的檢察官跑到香港機場的過境室裏面訊問,也就只有那一次筆錄,這樣子的一個問話是否有證據能力?這種就是請求偵查員直接在境外去問證人,那個案子裡辯方雖然很強烈地爭執但是最高法院好像是認為有證據能力,這部份的爭議其實比較敏感,因為也有一點像是台灣去行使司法的域外效力,但是這個舉證程序或者是說他的證據評價的方式是提供給我們檢方,所以這部份爭議也相對的算比較小,那比較大的是被請求方的偵查人在境外訊問證人,比如我們剛剛所講的,可能是日本的警察人員所以請他們直接在境外詢問證人,那這個又可以我國的人員參與的強弱的程度再分成兩種,第一種就是直接囑託訊問,等於有司法部的協助,那我就全權委託給境外方的被請求方訊問;第二種就是說就是請求方介入的密度比較高,請求方可能先預擬詢問要點,之後委託受請求方的偵查人員去問,甚至在問的程當中也參與一部分,尊重對方的司法效力但是我們人員也有參與,在詢問完了之後立刻做成勘驗筆錄證明,我方確實有參與,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這兩種裏面的第二種因為介入密度比較高的情形,其爭議可能比較小,比較具有證據能力。囑託訊問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最後一種就是所謂就是爭議最大的一種,就是並沒有司法互助協定,只是透過國際組織,例如:我們的刑警局跟國際組織之間的情資交換取得的證人筆錄,杜氏兄弟其實是這種情形。因為當時還沒有兩岸的共同協定,所以等於是說我國的刑事局跑去廣東佛山去那邊那拿到的筆錄,你要傳這些證人好像也傳不太到,最後認定這個筆錄有證據能力,所以這個境外證人的取證方式他是否具備證據能力會有討論的空間。 接著我們來討論舉證的蒐集程序跟評價程序,究竟是要用哪一個法。那原則上來講的話取得證據、去訊問這部份用的程序的法,原則上以受請求方的法律為之,主要原因是基於國家主權的尊重,畢竟是在他國境內去取證,所以程序上原則是依照被請求方的法律為之。但是取得證據之後要怎麼去評價證據能力的問題,原則上是以請求方─就是以台灣的法律為之,學者楊雲樺的見解是認為說因為刑事訴訟法是彰顯國家主權中的司法權,雖然在域外取得證據,但畢竟是要在國內宣判,所以說就證據法的部分還是依照是我國的規定。 那剛才所提到的這一個案例就是被請求方的偵查人員直接在境外去訊問證人─我們就是不要那麼繞口─就是其他國的警察在境外去問證人,他的證據能力在以往的最高法院有三派見解。 第一派採直接排除說,104年台上字第4813號判決,主要理由待會再講。共分成就是兩派見解,比較少數說認為國外的警察去詢問境外證人的證據的能力,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認為這是特信性的文書,有特別可信的狀況,採取如此的見解諸如104年度台上字的4813號判決,他是適用在大陸地區的公安筆錄;比較多數說是認為應該是類推適用到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以及之3,那採取這一派的見解主要是96年台上字第5388號以及大多數的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那同樣也是在處理大陸地區公安筆錄的問題。 現在來講絕對排除說,絕對排除說坦白說其實聽起來也是蠻合邏輯的,因為他主要是認為說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之3的規定主要針對的是被告以外之人,注意,是我國的檢察事務官、司法檢察官或者是司法警察的調查他們所為的程序,當然不包含說在外國的這個司法警察人員調查中所為的一個程序,所以說在剛剛所講的案子裏面的話,他認為日本的保安廳是屬於外國的人員,所以不能適用這個證據。 其中提到一個我覺得是一個蠻有說服力的一個理由,講到鑑於各國法律制度的差異跟實務運作的有別,被告的防禦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若通通以允許說類推、擴張傳聞法則的例外,將會侵害到被告的一個對質詰問權。
日本是一個文明的例子,我們講說今天如果是─沒有不敬的意思─比如說索羅門群島、史瓦濟蘭之類的,難道你會覺得說這樣的證據就直接依照我國的傳聞例外而可以用嗎?這是一個問題。還有就是說依照這個法律實務的這個運作,他認為既然是有所差別那應當要排除掉。 只是他會引起到的一個爭議是,首先這樣的見解可能有一點不是那麼國際化的潮流,可能還是要尊重我國的法治啦,所以說在這種情形之去處理跨境犯罪的時候,一律的把證據排除掉是不是讓案件會變得比較難去處理?這其實是採取絕對排除說的一個問題。 容許說裡面有分成兩個見解,首先這兩個見解都認為沒有辦法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的規定,有一派見解是認為是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認為因為是外國的警察人員或司法檢察官所以說沒有辦法直接去適用到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跟159條之3,但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的公務員也僅限於本國的公務員,而針對特定的案件也不是第2款的業務文書,大家都知道所謂的「業務文書」有「例行性」的一個要件,所以認為要依照第3款的規定去判斷是否為一個特別可信的狀況情形下情形去製作,當然是要綜合考量當地政經發展情況上或製作過程中內部與外部顯然具有足以相信內容為真實特殊的情況去判斷。但是這個地方可能會產生的一個問題是,首先筆錄當然是一個針對個案去製作的一個文書,不管再怎麼說其本身性質為為了證明犯罪而製作的文書,一定會有所謂的特別表現的請況。 但其實我國的筆錄也不是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去做處理,而是回到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如果用159之4例外地去肯認境外證人的筆錄有證據能力的話,那反而變成外國筆錄的效力還比台灣的筆錄更強?這樣很奇怪的事情,所以這一個說法算是少數的說。 多數說是認為類推刑事訴訟法第159之2、159之3,因為第159之2、159之3本來規定是本國的警察人員或是司法檢察官,但是這說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去例外去類推適用,但是要怎麼類推?能不能類推?這是多數說主要的一個爭議,主要法理是因為102年第13次決議允許類推,所處理的是所謂的第二類的證據,就是被告以外之人但不是用證人的方式(通常是共同被告),如果未經具結那他供述的證據能力大概會是如何的?最後該決議認為說去類推刑事訴訟法第159之2跟159之3的一個規定,因為當初法則在制定的時候盡量規定得很細,他們認為這不是容易排除的一個例外,如果你去允許說這種情形有證據能力,就是在檢察官前面但那要是有具結的供述。這一說認為如果這種情況下一旦否認它的證據能力,那反而效力就是變得很奇怪,警詢筆錄其實可以依照第159之2、159之3的規定而有這個證據能力,但反而檢察官面前詢問卻沒有證據能力,所以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就類推適用,就是說非以證人的身分就然後沒有具結的供述就類推第159之2跟第159之3。當初這個決議其實也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因為基本上刑法這邊算是禁止類推,至少是禁止不利於被告的類推,那但在那種情況之下為了方便所以去做這樣的決議,所以這一派的見解認為本於這樣的精神,「類推」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被禁止的,那但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如果我們可以綜合考量當地政經發展的情況上,或者是從事筆錄的過程及外部觀察,在例外情況之下的話可以去類推行是送送法第159之2跟第159之3。 本件的案例事實,2018年1月23號的決議有甲說、乙說、丙說。甲說是排除說,就是禁止去類推適用的,在做決議的時候甲說是0票;乙說認為在被告詰問權受保障的前提之下期性質上與我國警詢的筆錄雷同,同屬傳聞證據所以應該去做相同處理,因此是可以類推,等於是把剛才的多數說見解變成了乙說這樣子;丙說比較複雜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是整理我國各家學說的精華,原則上丙說不覺得可以類推,但是在符合一些情形底下例外去容許這個傳聞例外,比如國家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已經想辦法去傳人但都傳不到,又或者是其他不可歸責於國家的這個情形底下,又或者說已經某程度保障了被告的防禦權(比如說就是用遠距離視訊的方式去問了等等之類)。最後該決議採行乙說而不是丙,最後在評釋的時候丙說看起來好像就是很豐富結合了各家學說之長,但他沒有告訴我們一個可操作性的一個標準,所以說到最後多數的評量結論採乙說,那也造成了一開始提到的日本這個例子,其實有些人認為日本保安廳的這些筆錄都不能用,但是在漸漸的演進底下多數說是認為是可以去用的。 反而是大陸的公安這個筆錄,就是說日本的筆錄這個部份原本能不能用大家有爭議,後來大家才覺得可以用。但是中國大陸的筆錄大家都一直認為說可以用,這個東西大家會不會覺得心裏有一點點毛毛的啊?不覺得怪怪的嗎?這種法治比較沒有辦法預測的情況之下的筆錄……,我在猜想可能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問題,他可能不覺得大陸這邊是外國,當然大家會有很多不同的見解,但是在這種情形底下的認定標準比較寬、大陸公安筆錄的地位比較有證據能力,後來因為有這個兩岸共打協議─在這裏順便再補充,實務上認為說像這樣子的一個條約,比如我們跟美國之間也有簽類似像司法互助的協議,裏面有規定證據可以直接使用,這一個條約的先行的規定,他其實是一個傳聞的一個例外,所以美國那邊的證據如果是依照司法互助,這個部份我們直接承認有證據能力。那當然我們也跟菲律賓或斐濟都有簽有這樣的司法互助協定,但是因為每一個司法互助協定他規定的情形不太一樣,所以說就是像中非的司法互助協定就認為說可以就是自由的去認定,然後(17:40)…的話是根本就什麼都沒有規定,所以說原則上可能也只有在美國這邊才能夠直接用這個司法互助協定而去認為說這是一個傳聞例外然後取得證據能力,那其他國的話我們就依照這個傳聞法規去做判斷。 為了解決這樣毛毛的一個問題,日本文獻也有大陸所做的境外訊問筆錄的討論,最終日本平成的最高裁示也認定有證據能力,但是是在滿足一些件下才認為有證據能力。簡單跟各位報告,日本學者整理了這幾個判決而認為說,首先要如何對證據能力做評價呢?要充分了國際司法的偵查制的實際狀況,然後重點在溝通如何取證的時候,要特別要求做到日本容許做為證據而且易於肯定特別信用狀況偵查方法,簡單來講就是要用一個日本國人比較能接受的、比較文明、正式性比較高的這樣的一個偵查方法去取證,而且最好是日本的偵查人員在場作為一個擔保,要不然怎麼知道說就是你離開的時候會不會被公安擋之類的。最後利用在場日本人員的一個職務報告書跟證言去作為說證據容許性與特別信用狀況的判斷資料,簡單來說,可能日本人員報告說在取證的過程大致是符合我國這樣子,或是說普世共通的證據法則,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特別去容許有證據能力。
最終還是不能只靠這司法互助所取得的證據,還是要跟其他證據整合性地去判斷。有一個矛盾,就是說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很主要的證據,也要去看看說是不是跟其他的證據都有相符,綜合這些東西判斷下來之後才去判斷該境外取證的證據能力。
我們回過頭來,境外證據它的證據能力永遠是兩種觀點的拉扯,首先是懇認它有證據能力能使跨境案件的偵查變得比較容易,如果說一概地去否認它的證據能力的話,那跨境犯罪的這個部份可能很難去做偵辦。吳燦甚至在他的文章裏面就去講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不用把他們遣返回來,反正遣返回來的話因為外面有留的筆錄因為他們回來可以翻供,所以說境外筆錄都不能用的話你也沒有辦法判他。但是我們永遠會擔心說,究竟是什麼樣一個司法互信,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程序去採證,過程當中是不是符合普世價值比如說程序正義、公平審判,還有最重要的是不是有滿足到對質詰問這樣子的一個要求,境外證據永遠是這些部份拉扯。107年第1次刑事決議看起來是某程度認為是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跟159條之3的傳聞的例外,但在大法庭制度施行之後,究竟這樣的一個見解是否為不可挑戰的?究竟這個見解是否一定就去適用?舉例來說在他做成那個案件,做成這一個決議到今天為止,發生很重要的反送中的事件,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你會不會認為應該要進行什麼的程序才可以接受這樣的境外取證,那比如說新疆集中營裏面做的筆錄,或者說香港邊境看守做的筆錄,你會那麼相信嗎?很難說,所以說在時空背景有改變的情形底下反應我們是否要維持這個見解或者是說就是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一個標準提出來我們作為大家討論的一個原則,我的報告就這樣,謝謝。 尤伯祥律師: 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不曉得在座的各位道長對剛才元楷精彩的報告有什麼回饋? 沈元楷律師: 大家有沒有辦過這樣子的案件,就是採認他的證據能力的時候法院那邊沒有一個標準在那裏,因為昨天研究的時間就是說就是比較短,關於這個杜氏兄弟這邊的這個案件我大概也只是看了幾篇新聞沒有很詳細看他的判決,那我相信說在場的各位其實一定有辦過類似杜氏兄弟這個案子,那這案子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點,導致於說到今天大家還一直都覺得很有爭議? 與會者: 剛有幫我們整理了最高法院會議決議,那你剛剛還有提到一位學者的文獻,不知道可不可跟你請教是哪一位學者? 沈元楷律師: 李佳玟老師,吳巡龍檢察官也有寫文獻,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是偵查機關或是有這樣一樣背景出生、不管他念得多高,我看到的通常都認為這樣的情況有證據能力,反而是李佳玟老師─那篇文章還蠻值得一讀的─她應該就是丙說其中一個來源,我讀起她的文章覺得李老師其實似乎認為應該要採甲說、應該是要排除掉。 尤伯祥律師: 我自己的觀點是這樣,因為最高法院在證據能力上對於彈劾證據採比較寬鬆的態度,第一次的證據法沙龍我在評論最高法院107年決議的時候我就有講到,其實彈劾證據本身從來都不需要有證據能力,這個是最高法院一貫的見解,而且事實上彈劾證據從來沒有清楚的定義,換句話講,辯方今天不管拿什麼彈劾資料出來,只要合議庭這邊想要在有利被告之判決裡引用,是不需要有證據能力的。 所以今天討論的這個遊戲規則擴張了目前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的證據法則,事實上是朝有利於定罪的方向在走,對不對?邏輯很簡單,今天用來判無罪或者是有利於被告的判決的資料,本來不需要有證據能力,所以要是法院透過解釋或造法活動去放寬法律上的證據能力門檻,實際上就是降低了定罪的門檻或障礙,這種擴張在我看起來基本上都是要朝便於定罪的方向在走。排除說看起來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儘管排除說沒有去點到這個問題,但事實上最根本的問題是在這裏,最高法院可不可以以填補傳聞法則或證據法則漏洞的名義,自己創設朝向有利於定罪的方向的遊戲規則。 不過最高法院其實在證據法則上面,特別是傳聞法則上面做出這種所謂的超法規的傳聞例外並不是第一次,在其他的境外取證案例也有創設過超法規傳聞例外,在我以前做過一個農委會的案子裡。不過那個案子我是擔任告訴代理人,所以對我來講沒差。 那個案子裏面主要的定罪證據,是台灣駐新加坡辦事處的人員在新加坡辦事處的辦公室取得的訪談記錄。居然用沒到過臺灣的陳述者的訪談紀錄來定罪,完全沒有經過對質詰問,但是法院依然用了。在該案的最高法院判決書裏面,說這個是超法規的傳聞例外。我覺得現在有必要拿出來討論的是,以我們辯護人的立場來講,假使說你接到類似像杜氏兄弟這樣的案件,或者是我剛才講到那個新加坡案子,那是農委會發包的一個採購案,那個得標商真正的公司總部在新加坡,所以取證要去新加坡取證,辯護人對於境外取得的這些訪談紀錄、公安筆錄,或者是海上保安廳所做的筆錄也好,若要爭執證據能力的話應該怎麼爭執?這可能對我們來講比較實際嘛,對不對?元楷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爭執? 沈元楷律師: 可能還是先去調查做成的筆錄的情況,因為要去類推第159條之2跟第159條之3還是有些必定的要件,比如首先必須要有跟審判中不符,或者說他有一個特別可信的一個狀況,要在證據能力方面要去爭執取證的過程也好,可能就是沒有依照說我國的程序,甚至我看過有些人去質疑筆錄的做成規定,比如日本是沒有偵查中全程錄音錄影這樣子的規定,我們在這方面其實算是比較進步,就是說那如果說在沒有這樣子的全程錄音錄影,或者說在沒有辦護人在場的這種情況之下,那你怎麼樣去說明說他這個部分有一個特別可信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可能還是會從他外部周圍的狀況去做一個爭執,當然從法理上會去引用排除說那個最高法院的論述,但是刑庭決議做成了之後可能要去重新審視他做成的情形到底有沒有辦法符合例外,然後再去爭執證據能力的,目前初步的想法這樣。或者─雖然說我覺得這很難想像─例如可能沒有去告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尤伯祥律師: 告知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分兩種不同的情況,被告自己的筆錄或者是詢問紀錄最後再來講。我們現在講被告如何指認證人,先從最核心的證人,就是一開始就被當成證人來問的那一種情況。如果說今天是一開始就被大陸公安找來以證人的身分詢問然後做成的筆錄,我們怎麼去爭執它?如果說今天最高法院規則都已經訂出來了,就排除說我一律不採,你不要跟我玩這一套,你如果想跟我講排除說的話你去找大法官。假設是這樣子,那他用的是那個類推適用第159之2、第159之3,類推適用的這個遊戲規則底下我們開始玩。 沈元楷律師: 模式上可能只能去檢驗有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之2或第159之3的例外,如果是我,第一個先去攻擊他的採證程序或是說關於取證的規定,我國法律規定得不一樣而且比較兼顧到人權保障和對質詰問權等,先會從法治面去出發,然後其次就是從個案面去爭執在做成筆錄的過程中有無異常的情形。但是說實在話,境外取證要去看他有沒有什麼異常情形可能會更為困難,因為在國內你還有辦法透過跟被告對話覺得異常而去調查看看,在境外的情形很難去調查。 尤伯祥律師: 把它拆開來看好了,第159條之2是警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