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16 辯方證據開示座談會 側記5 尤伯祥律師總結與Q&A
日期:110.1.16 14:30~17:00
主持人:尤伯祥律師
報告人:陸梅吉教授、王緯華(Thomas Wang)顧問、秋田真志主任(李怡修研究員翻譯)
尤伯祥律師總結與Q&A
尤伯祥律師:
謝謝秋田律師,可以跟秋田律師報告,幸好台灣這邊沒有引進檢方開示,我們現在還是保持完全的開示,當時在反對檢方全面開示的官方理由裏面,確實就如同日本的說法一樣就是擔心辯護人或者是被告編造虛偽的抗辯,幸好這講法事實上沒有得到立法院的支持,所以目前我們的開示就只有辯方開示,沒有檢方的三階段開示的問題,那請問在座的道長們對於剛才三位報告人的那個發言喔有沒有要交流或者是提問的?
Q&A第1問
沈元楷律師:
請教各位報告人,第一個,辯方開示這邊的話,其實主要會影響被告不自證己罪以及防禦權,剛剛聽那個就是報告人所講到的,應該是說就是被告本身自己的一個供述或是他個人與律師間的秘密溝通特權不列在辯方開示的範圍。
在有一些情況,像王律師剛剛所提到共犯的情況,雖然說他可能是證人的一個訪談,但是這個證人可能他有很多事情,關於說證人或者是這個證人等於有可能是共同正犯的一個情形底下,可能涉及到說就是被告的這個不自證己罪或者是防禦權的權利,這個部份究竟要不要開示以及開示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第二個問題,剛才秋田主任在報告提到在日本這方面的話就是如果說是辯方的開示其實只要開示一個summary就好了,那我想瞭解的是說所謂的summary是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啊?這部份其實除了日本的那個秋田先生之外其實也很想請教陸教授還有王律師。

王緯華顧問Thomas Wang:
第一個,如果你沒有要提出這個證人,以辯方的角度你就沒有必要去開示,因為辯方,我們是只有我們要找這個證人的情況下,我們才需要開示。
如果你說我現在建立在如果這個人證人會作證的狀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要考慮的是從這個證人的出發點,他有沒有constitutional privilege比如說他跟他的律師有沒有對談?或者他講這句話會不會自證己罪?如果會的話,我們會把能夠受到privilege的部份把它redact就把它那個黑掉這樣子讓外面看不到說這一部份講的是什麼。
如果說不是你的被告,是共同被告的話,我們會以共同被告他自己本身的權利出發,很多人都說不自證己罪這個東西是絕對的權利,是嗎?其實不是喔,如果你沒有可能被定罪那你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所以檢察官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可以給所謂的immunity所以他保證你、無論你做什麼樣的證詞你都不會因為這個證詞而被起訴而被定罪。
美國就有一個笑話,檢察官最大的噩夢是什麼?比如說今天我們兩個人是共同被告,檢察官跟你說你知道是誰做的對不對,我給你有絕對豁免權我絕對不會起訴你,做陳述都可以,可是你一定說實話,好嗎?你說好就簽字,然後到了陪審面前你說:我做的。所以檢察官很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可是因為很不願意這樣做所以你的Fifth Amendment、不自證己罪的權利就會存在,所以兩方的律師各自會為各自的客戶去主張。
陸梅吉教授:
我補充兩點,紐約州的新規則,你可以看some point about discovery ,always remember that defense discovery item that intend into use,如果你不要使用證人的證據,你不必給檢。所以有的時候,可能要判斷只是跟那個人在一起聊天或決定真的是要使用他是證人。
有辯護律師說,他就是跟我就是聊天或問我一下。比如說關於中國的法律,中國人在美國犯罪,所以有的時候可能中國的法律有有關係,他說我不要你當證人,我就是要跟你打電話,然後可以聊天,如果這樣的話,是沒有什麼證據開示的一些義務。
第二點,關於privilege,有的州不一樣,比如說marry law privilege,平常是一模一樣,但是那個州的法律有的時候有區別,所以你必須很仔細地看那個州的法律。
尤伯祥律師:
剛才沈律師的第二個問題,那個summary到底要寫到什麼程度?這個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我們在國民法官的第一次模擬審判裏面被檢方要求要開示,我們非常的憤怒,因為我們跟證人訪談的紀錄,檢方要求我們要開示,這個對我們來講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後來我們決定畫一隻烏龜送給檢方,當然檢察官很生氣,所以我們還是被逼著要多少寫幾行給檢察官,那我不曉得美國這邊是怎麼做的呢?
王緯華顧問Thomas Wang:
Summary他寫的其實很簡單就是material statement,要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呢?我自己的處理方式就是,想想看我有哪些東西我會不寫出來,任何不寫的東西,我就會想說我什麼理由不寫它,它是不重要?它是privilege?還是它有別的理由我無須開示,從這三個出發點你就可以把絕大部份的先處理掉,反過來你在問你的證人的時候,尤其你現在沒有開示義務的時候,你問證人的時候你要比較有技巧性,你不要問,有沒有其他你想要告訴我的?還是告訴你一些秘密,你真的很不想知道的事情?證人就要做這種事,所以你就要比較精確一點去問,那天那個時候在不在場?不在,good, perfect, leave it alone. 你不要繼續問他,後來就得說他跟我說不在,就很尷尬。所以這是兩點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是你自己問問題的時候小心一點,另外一方面是,小心問問題之後得到的如果真的對你不利的東西,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開示,你全部寫出來之後,有沒有什麼原因可以把它刪除掉?最常見的就是privilege然後再來就是 materiality對你的主張影響。
聽到不利的東西在律師倫理上就不可以,可是所以像我自己如果我知道這個證人很可能會有就是雙面刃,我在開始前我就先跟他說,今天你跟我的對談如果我打算請你去作證,我需要提供給檢察官,所以你跟我的對談是不受保密的,今天問你的問題,我希望你就是針對我的問題回答就好,這保護你也同時保護你的朋友,OK嗎?好,那我現在開始問。
你就可以witness control,控制這個證人,他會告訴你什麼資訊,你自己寫好,就避免就這樣子的麻煩,這個是完全OK的。
秋田真志主任、李怡修研究員翻譯:
現在給大家看到的就是剛剛講預定證人會講哪些東西的summary(秋田真志主任以螢幕分享),預定書面,包括封面是A4兩頁多一點點的內容。這是一個SBS的案件,這個證人是個醫生,實際上詰問的時候大概是40分鐘到50分鐘,其實大部份當然就是對被告有利的一個東西,剛剛有問到共犯證人有沒有不自證己罪的問題,因為我們萃取的這個證據其實都是檢方那邊過來的,所以其實即便我們沒有寫在這個預定證明的書面裏面,檢方其實都已經都掌握哪些事情對被告不利,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必要把它寫在這個summary裏面,檢方應該要自己處理。
尤伯祥律師:
謝謝,看起來怎麼去寫這個summary學問很大,搞不好需要再開一些課程來教大家怎麼寫辯方開示的summary,也許Thomas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你們在美國這邊怎麼做summary的一些方法,還有一些示範性的書面,可能也要拜託秋田主任這邊是不是也可以除了提供這位專家證人的意見之外,一般的證人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書面的資料讓我們參考要怎麼去製作。那不曉得現場的道長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Q&A第2問
林楊鎰律師:
今天來這裏非常高興,請教陸教授,參考資料第十頁有提到說檢方違背證據開示法律效果,雖然我們台灣目前是檢方要全部開示,可是你難保他不會隱藏,應該這樣做可是他沒有做,因此這個點還是有它的重要性。
教授有提到檢方不能抗辯說東西在警察那邊。如果違背證據開示的情況嚴重時被告的罪名可能會被撤銷喔,那嚴重的情況為何?第二點,剛好美國這個檢察官也是透過律師公會來懲戒,那這個是有關行政的部份是如何懲戒?
最後一個問題,問王顧問喔,剛提到說當一個被告持有兇刀或文件給律師的時候,只要律師他不是在隱藏,沒有控制它,我知道都沒有關係。
假設被告他持有比如說槍也好那兇刀也好,要拿給你,你說你自己保管好,他聽你的話自己保管好,那這個東西算不算是你律師呃一樣在控制的範圍?

陸梅吉教授:
非常好的問題。我想最重要就是每個法官可以選擇要怎麼裁量,每個州不一樣,每個法官也不一樣。有的時候如果是檢察官是故意的惡意的不給辯方,嚴重的可能法官說我就排除,你不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就是證據很多,還是他們很忙不是故意的,就是沒想到警察還有那麼多的證據,平常就是給你多一些時間,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準備好,extend time。
有的時候警察play games,法官可能會生氣。還有你可以看就是還有那個disciplinary proceeding,還有一個可能性:如果真的是故意,把什麼都很重要的一些證據就放在桌子上,不給辯方,可能還是有State Bar的ethical,也有一些自己的程序,對他status as a lawyer也有影響,這個很少。
例如十年前的北卡羅來納Duke大學,有幾個運動球隊的學生成了被告,全美國關注這個大案件,所以檢察官天天就是跟媒體採訪,然後就被發現還有證據沒有給辯方,甚至是惡意的偷藏證據,以後North Carolina state bar認定他不可以當律師不可以當檢察官,這對全美國的檢察官律師有deterrent effect。
但是平常就是,晚了或我現在才發現了這個證據,法官說好,我們就等待一個月還是一個星期。
王緯華顧問Thomas Wang:
先補充第一個問題,首先建議,如果碰到Brady Violation的這種狀況,很多律師都犯了錯是,你會想要把remedy,怎麼處理跟是不是有犯錯混在一起談,因為你混在一起談的時候檢察官都會說我不是故意的,而法官就說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們不要嚴重地去懲處。
可是倫理他上面寫的是irrespective of the good faith or bad faith你前面是惡意的、你善意的也好,總而言之你的疏失造成了這個無辜的人需要多坐一個月的牢,那是實質的後果,所以其實Brady從來就沒有在意你到底是惡意還是善意,當我們在做這個argument的時候我們也是要同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如果我自己的方式的話,我選motion我只會選出一個Brady Violation, , remedy是什麼我容後再議,我先法官說你先決定是不是一個Brady Violation,很明顯你就是沒有交出來,有Violation,停。
我們再來說這個violation我們要怎麼處理,那就像陸教授說的我們很常聽到的是給你多點時間,給你多點時間,可是我的客戶如果他有交保在外面那算了,如果還沒有交保繼續在牢裏面關著,我會跟法官說,為什麼檢察官的疏失需要讓我客戶多待一個月的牢?你可以解釋一些理由嗎?那他可能會說他不是惡意的,我說這無關,重點是事實發生了,即便他真的是good faith,who cares?The point is: my client is in jail你把他放出來,你把他放出來一個月我可以接受,你不能說你又要延長,為什麼我的客戶要幫檢察官的疏失買單?你已經承認是他的疏失了,所以你要把這兩個切開來去跟法官爭辯,要不然,法官混為一談的時候,永遠都認為他不是惡意沒關係。
經驗上來說,紐約我知道有一個檢察官,他自己說是疏失,後來是被法官規定他永遠不能踏入法院打任何案子,然California有些state bar proceeding也是一樣,就是因為這樣子檢察官被除去了他的bar license,所以至少我們在美國來講,就想說你做了一個prosecutor你最容易失去你的bar card的原因就是Brady Violation,easiest way to lose your bar card當然不是說很常見,但是最常見。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的處理方法是,我會非常非常非常嚴厲的告訴他,如果這個東西交給我,依法我一定要交給檢察官,我不會拿起來。你拿出去之後你要做什麼,你都沒有義務跟檢察官說,我會給他一個然後leave it at that讓他自己去領悟,我已經把你帶到門口了,已經告訴你了你交給我了我一定要交給檢察官。你帶出去,你想要把它做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剛剛目前為止講的一切都是attorney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我沒有叫他做什麼非法的事,你不能跟他講說你就把它銷毀,如果你叫他去把它銷毀你就要把它丟到海裏,那你是教唆他去犯罪,就有abuse of attorney-client privileg,所以你不能跟他這樣講,可是你可以跟他講你拿出去之後你做什麼我都不需要跟檢察官說,那是OK的。
就是一個倫理線要踩穩的地方,即便類似這樣的情況我一定會record做得很清楚,保護我自己也保護他,如果檢察官哪一天發現了他說我是故意隱匿的,我說沒有真的我有紀錄,我可以給法官看我當時跟他說什麼,我自己做好紀錄保護我也保護他這樣子。
沈元楷律師:
Thomas精闢的回答我也學起來了,我想cue一下尤律師,在我們台灣這邊的話也是同樣的一個狀況嗎?
尤伯祥律師:
剛才的兩個問題,其實都涉及到職業倫理。
先講第二個問題,那確實是有律師倫理的問題,所以如果是我來處理的話處理的方式也會跟Thomas一樣,我不是檢察官發現真實的工具,我也不是檢察官用來證明我的當事人有罪的工具,所以我的當事人在我的會議室裏面,即便跟我亮出那一把兇刀給我看,當然我不會讓它留下來,我也不能夠叫他銷毀或者是拿去把它隱匿起來,但是我絕對會跟他講說你現在最好把它拿走,你如果留在我這邊的話,我就必須要交給法庭,因為我們的律師倫理規範有一個對法庭誠實的義務,對法庭誠實的義務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不能夠妨礙司法調查,我如果利用我跟當事人之間的保密特權隱匿了這一把兇刀或者是這個兇器,那麼就是妨礙司法調查這個是絕對違反律師倫理。
在台灣,我舉一個例子,以前有一個影集叫律師本色,那裏面有一集有一個律師在那個上班途中接到他當事人打來的電話,拿起來就講說,我現在在路上被警察攔下來了,然後警察對我做酒測,那律師就很不耐煩地跟它講說「那就測阿」「可是問題是我在一個小時之前才剛從酒吧出來」。
那律師想了一下以後就跟他講「這樣啦你車上還有沒有酒?」因為他知道這個當事人車上都有酒,所以那個當事人就講說「有啊」「你現在趕快把酒拿起來開始灌」,那個當事人就聽他的話灌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瓶,灌完了以後就不能酒測了,但這個律師後來被懲戒了,因為這個就是妨礙司法調查。
前面檢察官違反Brady的情況,我的看法是這樣,這個在台灣真的是到目前為止,檢方的開示沒有任何的擔保可以要求他們如實的開示。目前為止我們制度上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讓檢察官乖乖的開示,就是檢察官倫理,只有檢察官倫理有辦法迫使他們乖乖開示,但是如果你要用檢察官倫理規範來迫使檢察官乖乖開示的話,那麼就跟剛才Thomas所講的,其實Brady的違反重點是在權利的損害而不在於過錯,這剛好就有點不太一樣,這沒辦法因為兩個國家的制度不一樣。我們到目前為止其實沒有任何一條規定去處理檢方隱匿證據或者是檢方把證據給遺失掉了,甚至法院把證據遺失掉了該怎麼處理。
邱和順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邱和順案裏面兩個關鍵證據在審判過程中不見了,第一個是勒贖的錄音帶,另外一個是有疑似是兇刀跟疑似兇手的衣物的黑色塑膠袋,兩個都給法院在審判一半就搞丟了,我們連是在檢察官那邊搞丟的,還是在法官那邊搞丟的都不清楚,可是這個事情在我們的訴訟法上面怎麼去處理?沒有。
所以那個倒楣鬼,現在還在牢裏面等著接受死刑的執行喔,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前面那個問題我只能跟你講,那個可能會構成檢察官倫理的違反。
補充與總結
秋田真志主任、李怡修研究員翻譯:
剛剛講一般證人不是專家證人的時候的狀況,我想要再分享一下。這個就是一般證人的狀況,那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也是一樣就是寫出有利的方面的主張,一樣就是只有兩頁。大概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summary。畢竟那就是辯方的開示所以把我們的牌給對方看了,這個畢竟還是對我們自己有負擔。
有一些狀況甚至檢察官會說我想見一見你們那邊的證人,當然證人是沒有義務說一定要見檢察官,但是有一些案件會發生這種狀況。在日本現實上就是一般人如果被檢察官說我們來聊聊天或什麼的,一般人可能很難拒絕檢察官。
如前所述,很高興台灣維持著全面證據開示,希望繼續維持。
王緯華顧問Thomas Wang:
我想到兩個可以供大家參考的議題,一個是這個人他可能犯罪,隔天他就去找律師他就簽了那個retainer agreement,請了這個律師做了他的辯護人,他的辯護是「不是我做的」。
檢察官是案發後的一個禮拜他才開始調查這個人,那如果你真的不是你做的你怎麼會在隔天在檢察官還沒有調查前,就開始知道找律師呢?所以這個律師他的retainer的date本身就會非常非常重要,當時這個案子的狀況就是,檢察官他就是覺得這有什麼不能問的?法官也覺得很奇怪就是When did your clieent hire you? What’s the big deal?
可是在這個案件裏面有有絕對的重要性,那我知道台灣也要對法院提狀之類的東西,這個日期到時候要抓一下,可能會出錯。
另外一點,假設我今天真的不得已我聽到這個證人說了對我客戶不利的話,我們的法律上規定我一定要把這個提供給檢察官,這時候其實有時候個ethical的問題,我同時我要對我的客戶的權益負到最高責任,如果我幫他辯護會對他造成損害,我是不是應該抽身?我是不是應該拒絕繼續做他的辯護人?
就像我這邊有講到obligation去disclose,檢察官也不能問我因為那是我是因當事人我還是他的律師,所以這個可能要思考一下,如果是決定性的證據,我只要提供給檢察官我的客戶必敗,可能會被判死刑,那在律師倫理上我能不能夠在他一定會被判死刑的情況下繼續幫他辯護,還是我應該抽身,告訴他的新律師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抽身。
因為我跟我的客戶之間我們有communicate我們有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我永遠不會告訴你為什麼抽身,可是我是不是應該抽身這是大家需要考慮的一個ethical的問題。
尤伯祥律師:
相信大家今天收穫滿滿豐富,謝謝遠在線上的秋田主任與怡修博士,以及到場的Thomas Wang、陸梅吉教授。
<座談會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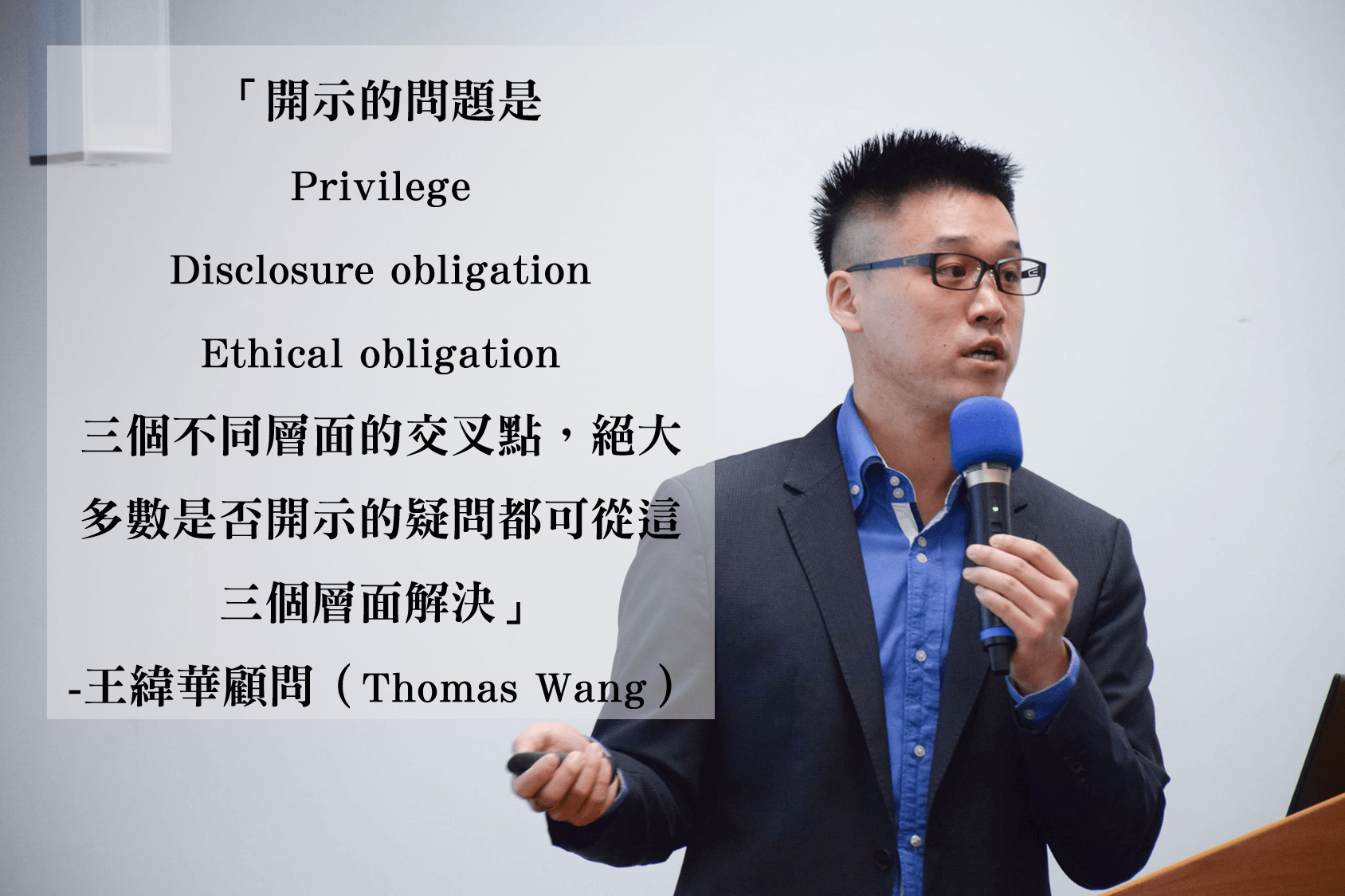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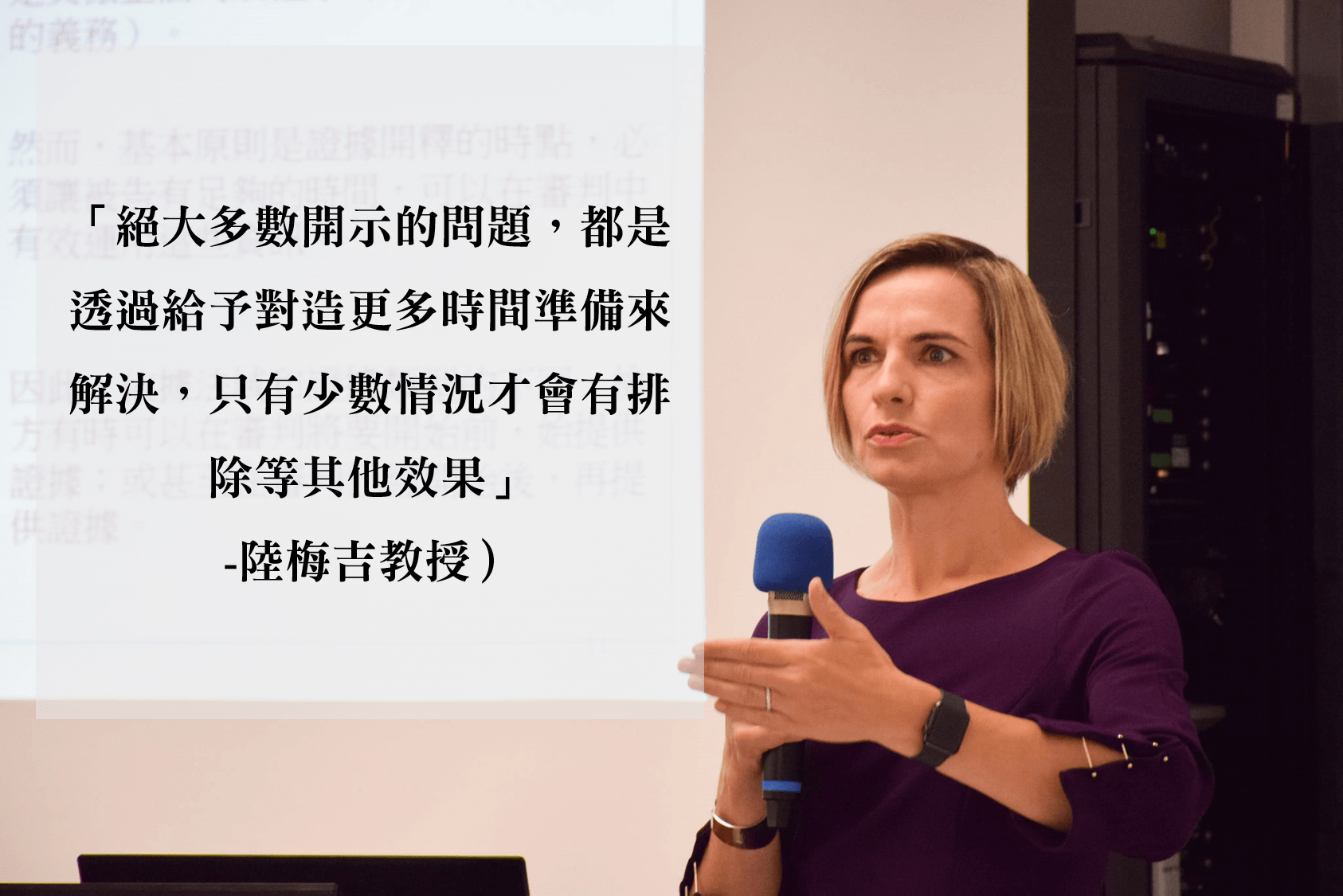
我要發問
想要參與討論嗎?請在下方寫下您的留言。